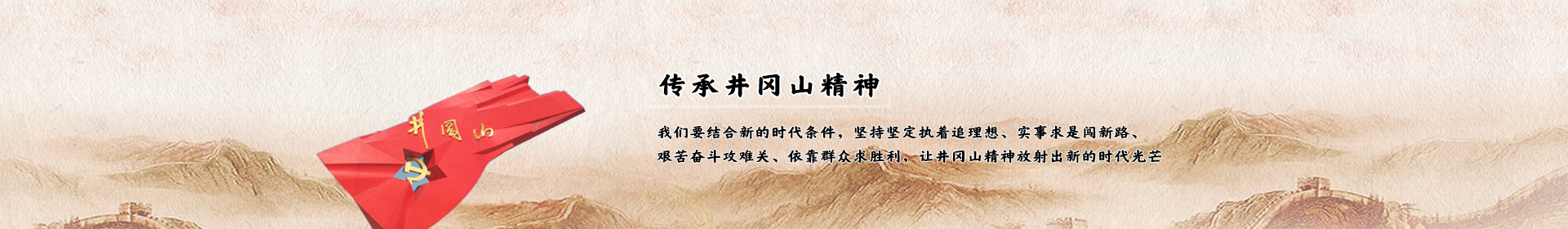【鄉居舊憶】枇杷熟了
窗子下枇杷熟了,園圃里枇杷熟了,村道邊的枇杷也熟了。
細雨茸茸濕楝花,南風樹樹熟枇杷。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熟梅天氣半晴陰,摘盡枇杷一樹金。這些趙宋與朱明王朝詩人筆下枇杷,串起紫色苦楝花火紅石榴花,以及留酸齒牙的楊梅果,在鶯飛草長的江南時序里次第展開。

噢,還有桑葚。鄉居的屋后,有株老桑婆娑,朱紅鳥黑桑子如夏夜繁星綴滿枝葉間,風雨后,一地狼藉。桑子枇杷鄉間果,稀松平常并非珍,而對于生長于所謂一線城市的童孫,從來只知在超市貨架上尋覓,或從快遞小哥手中接獲可食物,現能自攀自摘現取現啖,則是從未過的體驗而樂不可支。
南宋詞人辛棄疾《村居》:最喜小兒無賴,溪頭剝臥蓮蓬。這客居信州鄉間的齊魯硬漢,捕捉到這種鄉間童趣!
童孫樂,我禁不住憶苦思甜。
我輩童年,與人工培植的瓜果極少有緣。能生食的只土里刨出的蕃薯花生,或尋得的野果,如草莓楊梅毛栗貓牯卵(獼猴桃)。那時沒流動商品,方圓三四公里一個國營購物點,僅售賣火柴煤油及憑證限購的布匹等日用品,半自給農村經濟。

而村民似乎只知藝稻,沒有瓜果種植傳統。肇基400多年吾村,那兩位明季、準確說是清王朝創始人努爾哈赤出生那年徙此定居的兄弟二人,他們相中這有山有水有平疇風水寶地作家園,易耕,宜居,我對這倆祖宗一直敬崇。唯一不滿,他們沒種下百年老樹,也沒教導子孫在房前屋后多種樹,風景的,經濟的,如桃,或梨,弄得我們落籍于此,從小不知果味。
每年端午前后,難得進一次小縣城的父母,帶回幾根黃瓜都童涎三尺。成人后集體勞作,有對年青夫婦出工前分食了一個蘋果,勞作時作談資炫耀,大家覺得那女的打的嗝還飄著蘋果的香味。真的,沒騙你。

鄰村村后河灘,種了幾十棵山李樹。仲夏,如算盤珠子大小的山李半熟,果皮泛點紅暈,咬之略甜卻酸,鄉童垂涎之,常三五結伴去那小河裸泳,以拔河底水草喂豬作幌子,覬覦,伺機往樹上扔石塊,砸果于地,撿拾,迅即溜回水中。主家或嗔怒,如杜甫茅屋歌云:南村少年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童頑或如魯迅的《孔乙己》,讀書人偷書不算偷,算竊,好么?小孩偷果嘗鮮不算偷,鄉俗如此,民風如此。

本村當時有3棵果樹。一棵是樟樹藥商落戶我村開藥鋪,種了棵主要是藥用的枇杷,另兩棵是入贅我村的鄰鄉人所帶來山棗樹。如今遍植村里的這兩種樹,是百多年前移民文化無心插柳的意外溢出效應。有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吾村百余年前僅20余戶農夫,因宜居,女多不嫁出村,60年前接納過一些自湘自粵自閩的逃荒壯男,近幾十年的大流動,已是縣道通途的山鄉小鎮,竟有100多戶,且是十數省籍的中華小聯合國了。
一顆枇杷,或是微篇《食貨志》,可品讀出遷徙流動,庶民經濟,鄉村的發展與變遷。
(5月1日寫于鄉間)
作者簡介:吳志昆,男,作家,文化學者,退休公務員。
??以上就是 【鄉居舊憶】枇杷熟了文章的全部內容,如果您有井岡山培訓,井岡山紅色培訓,井岡山紅色教育方面的需求,可以隨時咨詢我們。 本文鏈接:http://www.jgspx.com.cn/jinggangfengguang/2020/0503/1814.html 轉載請注明出處!
??聲明:本站內容及圖片如沒注明出處則來自網絡,無從考證來源,僅用于公益傳播,如有侵權請在后臺留言或直接聯系我們告知刪除或標注來源,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