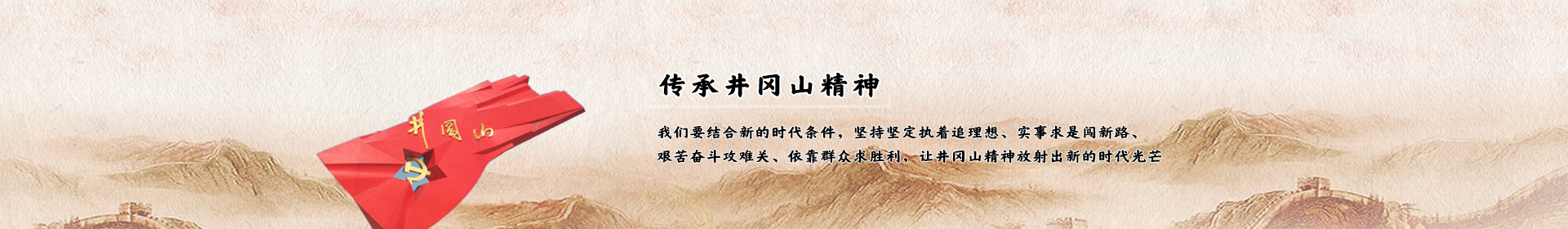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日中午,黨和紅軍主力渡過了湘江,經(jīng)西延區(qū)向老山界前進。以后幾天,驚魂甫定的中央和紅軍急于脫離險區(qū)。康克清在《回憶錄》中說:“這里高山峻嶺,森林茂密。敵軍被甩在后面。敵機難以偵察,可以稍事休息。一個多月的緊張奔波,總算可以喘口氣了。”到4日,開始考慮去向問題。
12月8-11日,軍委二局兩次截獲國民黨軍電報:蔣介石已集結(jié)四五倍于紅軍的兵力,布防于紅軍北上湘西途中,意欲將紅軍圍殲于桂湘黔交界地。若紅軍北上湘西,勢必一頭撞進蔣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陣,一場實力懸殊的決戰(zhàn)在所難免。是硬闖第五道封鎖線,還是轉(zhuǎn)兵避其鋒芒?成為擺在紅軍高層面前一個生死攸關(guān)的抉擇。
12月12日,軍委兩縱隊(即野戰(zhàn)司令部、軍委第二縱隊)到達芙蓉,中央部分領(lǐng)導(dǎo)人在芙蓉木林庵召開緊急會議,就北上湘西還是西進貴州展開了激烈爭論。伍修權(quán)在《我的歷程》中說:“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qū)時,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察覺我們的意圖是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在我們前進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強大兵力,形成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nèi)ャ@。面對這一情況,李德竟然堅持按原計劃行動,把已經(jīng)遭到慘重損失的三萬多紅軍,朝十幾萬強敵的虎口中送。在這危急關(guān)頭,毛澤東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yīng)該改變戰(zhàn)略方向,立即轉(zhuǎn)而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軍覆滅之災(zāi)。中央迫于形勢,只得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毛主席的意見被通過了。于是部隊就改向貴州進軍,這就一下打亂了敵人的原來部署。”
鑒于長征初期減員嚴重等原因,為提高基層戰(zhàn)斗力,以便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中革軍委從1934年12月13日至19日在湖南通道、貴州黎平期間進行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整編。整編令是在通道縣發(fā)布,而關(guān)于整編的宣傳、解釋、合編等則是在黎平境內(nèi)進行和完成的,故稱“黎平整編”。13日,軍委兩縱隊宿營于今通道縣播陽鎮(zhèn),發(fā)布整編令。14日,軍委兩縱隊宿營于今黎平縣洪州鎮(zhèn),且開始合編。17日,軍委兩縱隊進入黎平城,紅五、八軍團到中潮地域并開始合編。19日,軍委第二縱隊并入第一縱隊合組軍委縱隊完成,并離開黎平城到高場宿營。21日,軍委縱隊從黎平下八里出發(fā),至錦屏瑤光宿營。
關(guān)于通道會議,有少數(shù)人常糾結(jié)于三個問題:第一,會議名稱。通道會議曾有飛行會議、軍事會議等之稱。其實,會議的重要性和名稱不一定有關(guān)聯(lián),如1927年“八七會議”也僅是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第二,通道轉(zhuǎn)兵的性質(zhì)。從主觀動機來看,通道轉(zhuǎn)兵是戰(zhàn)術(shù)轉(zhuǎn)兵,但在客觀上卻成了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轉(zhuǎn)兵的第一階段(1934年12月13-17日)的開始。所以,它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第三,會議召開地。現(xiàn)定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通道轉(zhuǎn)兵會議會址”是縣溪,筆者則認為應(yīng)在芙蓉。根據(jù)伍云甫的《長征日記》、陸定一的《長征大事記》等綜合得知:12月12日,中央和軍委主要負責人宿營于芙蓉。他們?yōu)槭裁匆峤筮h,不在宿營地而去30里外的縣溪開會?其實,只要是在今通道縣境內(nèi)開的會即可稱為通道會議。如果說轉(zhuǎn)兵會議是在芙蓉召開的,也可叫通道芙蓉會議妥當,因為芙蓉當時屬綏寧縣(1951年才劃歸通道),承認通道芙蓉轉(zhuǎn)兵會議會址,才是真正促成"牢記使命,不忘初心"。
黎平位于黔湘桂三省交界處,山高林茂,有利于紅軍蔭蔽集結(jié);紅軍突然轉(zhuǎn)兵貴州,使蔣介石難以重新調(diào)兵遣將堵剿;亟待通過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來確定新的戰(zhàn)略方針,在紅軍入黔第一城——黎平討論解決十分及時;地方軍閥自打小算盤,使貴州防守力量薄弱;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的“鐵黎平”城高墻厚,易守難攻;黎平城物產(chǎn)豐富,便于紅軍補充給養(yǎng);受紅七軍、紅六軍團過黎平的影響,群眾基礎(chǔ)較好。有鑒于此,中央決定在此略事休整并召開政治局會議。
12月18日,在黎平古城翹街召開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黎平會議。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云、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等人參加。李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其意見則由博古帶到會上。
會議實質(zhì)上是繼續(xù)討論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最后否定了“左”傾領(lǐng)導(dǎo)人提出先西進貴州黎平、錦屏,后北折黔東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錯誤意見,采納了毛澤東深入貴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根據(jù)地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guān)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第一,“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jīng)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jù)地區(qū)應(yīng)該是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yīng)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在不利的條件下應(yīng)該轉(zhuǎn)移至遵義西北地區(qū)”。其實,軍委早已在17日的《關(guān)于我軍各部十八日的行動部署》指出“一軍團應(yīng)……對劍河、天柱、錦屏各方向偵察、警戒,并準備占領(lǐng)劍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進”。而此前的中革軍委的電令都是部署北上湘西的。第二,“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zhàn)軍之動作應(yīng)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yīng)力爭避免大的戰(zhàn)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yīng)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qū)前進”。第三,“為著保證這個戰(zhàn)略決定之執(zhí)行,堅決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
周恩來在1943年的《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fā)言》中指出:“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wǎng)。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jù)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陳云于1935年10月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紅軍西征時說:“在黎平,領(lǐng)導(dǎo)人內(nèi)部發(fā)生了爭論,結(jié)果我們終于糾正了所犯的錯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lǐng)導(dǎo)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邊界,敵人集結(jié)了四五倍于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
顯而易見,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長征以來的首次戰(zhàn)略轉(zhuǎn)兵——不去湘西去黔北,使從通道會議開始的轉(zhuǎn)兵得到了實質(zhì)性的發(fā)展,開始了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轉(zhuǎn)兵的第二階段(1934年12月18-31日),從而使蔣介石在湘西消滅中央紅軍的夢想化為泡影。
12月19日,《關(guān)于軍委執(zhí)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之決議電》發(fā)布。一是分成左右兩個縱隊向黔北進軍。二是為迷惑敵軍,軍委規(guī)定各部在進行到施秉、黃平地域前,用正常行軍速度前進,使國民黨軍認為紅軍仍在北上或西進中徘徊,以造成錯覺。同時,軍委電令紅二、六軍團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造成策應(yīng)中央紅軍北上湘西的假象。“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以致后來的四渡赤水也被蔣介石認為“紅軍反復(fù)徘徊于此絕地,乃系大方針未定的表現(xiàn)”。
21日頒布的《總政治部關(guān)于創(chuàng)立川黔邊新根據(jù)地工作的訓令》,旨在加強對指戰(zhàn)員們進行政治局決議的解釋、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等工作。主要是指出中央紅軍總方針為“轉(zhuǎn)移作戰(zhàn)地區(qū)創(chuàng)立新蘇區(qū)根據(jù)地”,當前的偉大任務(wù)“是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qū)創(chuàng)造新的根據(jù)地區(qū)”,并要求各級政治機關(guān)的政工人員做好政治局決議的宣傳解釋工作。
通道會議決議和黎平會議決定,顯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此后紅軍以勢如破竹之勢,穿州過府,挺進黔北,扭轉(zhuǎn)了長征初期的不利狀態(tài)。陳云在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西征時說:“當我們到達貴州時,紅軍已不再是經(jīng)常不斷地被敵人攻擊、四處流竄的部隊,而變成了一支能戰(zhàn)能攻的有生力量。
??以上就是黎平會議文章的全部內(nèi)容,如果您有井岡山培訓,井岡山紅色培訓,井岡山紅色教育方面的需求,可以隨時咨詢我們。 本文鏈接:http://www.jgspx.com.cn/hongsejingdian/2020/0813/1977.html 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
??聲明:本站內(nèi)容及圖片如沒注明出處則來自網(wǎng)絡(luò),無從考證來源,僅用于公益?zhèn)鞑ィ缬星謾?quán)請在后臺留言或直接聯(lián)系我們告知刪除或標注來源,謝謝!